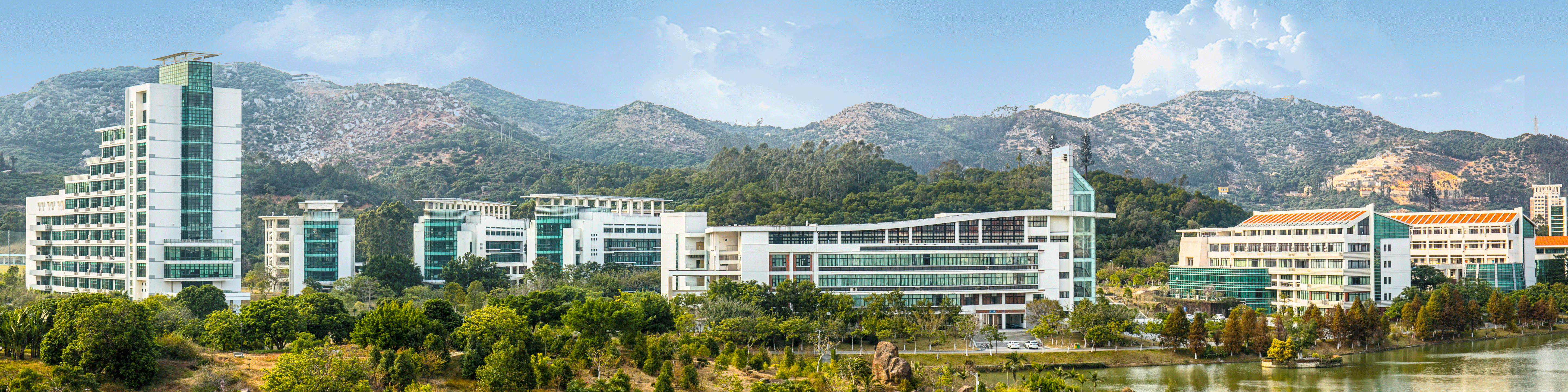科研平台
环保总局副局长:“特殊利益”正成破坏环境首恶
人员机构2007-01-18
<'提要'> 潘岳称经济增长方式不转变,环保不会有明显起色,环保法律虽然多,但多停留在理想主义阶段,惩罚权十分有限。第三次环保风暴动用“区域限批”已是最狠的行政手段,再往上,就该追究行政责任了,而某些“特殊利益”是环境恶化的主因。
2007年1月10日,“环保风暴”又起。4个市和4个电力集团的建设项目全部被停批、限批——风暴之猛,史无前例。
风暴策源地在北京官园桥路口,国家环保总局淡绿色的九层楼里。它的对面,中国国电约20层的大楼矗立着,“楼这么高,把我们的风水全挡住了。”环保总局的人士开玩笑说。
但这次,风水似乎轮流转了。总局宣布“区域限批”后,包括国电在内的几大电力公司股价应声而落——真打痛了。
1月15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接受了采访。
本报发稿前有媒体报道,潘岳“升任环保总局第一副局长”。但据记者了解,此消息不确实,环保总局并没有“第一副局长”的称谓。最近因为两位副局长退休,潘岳排名自然靠前,谈不上“提升”。“潘旋风”担任副部级职位,已有13年。
“特殊利益”,环境恶化的主因
记者:2007年“环保风暴”,你们用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手段——区域限批。决策过程是怎样的?
潘岳:这个想法,我在2005年第一次环评执法时就有了。但是当时连环评法都没人知道,一下子就“区域限批”,震动太大。所以我们决定先从“普法”开始。2006年第二次环评执法时,我们对形势还是过于乐观——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每年节能 4%,减排2%”。结果是,2006年主要污染物排放不降反升;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突发性环境事故,群众环境投诉增加了三成,中央领导对环境问题的批示比上一年增加了52%。我们意识到,对这种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扩张的高峰,温和手段已不起作用。所以,我们使用了这么“狠”的手段——环保总局成立30年,此前从没使用过。
另外,2006年12月新开工项目清查专项工作中,环保总局已与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国家安监总局等7部委形成共识,今后将逐步对各项建设程序执行不力的地区,采取暂停项目审批或核准。但新的制度要经过试验,环保总局先踏出这一步,成功或失败,都将为其他部门提供借鉴。
记者: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十一五规划又将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作为约束性指标,现在又进行宏观调控,但2006年仍然成为中国环境形势最严峻的一年。症结到底是什么?你以前说是“扭曲的政绩观”,但不执行中央政令、乱上项目,中央也没有将其视为地方官的政绩。举个例子,中央处理内蒙古新丰电厂事件,也处理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负责人。
潘岳:我曾一再强调,环保首先是政绩观问题。但现在,一种特殊利益结合现象正在和错误的政绩观一起成为环境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
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疯狂扩张中,产生了一种特殊利益结合现象。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通过上大型重工业项目,追求短平快的业绩;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庇护下,一些企业把全民的资源环境变现为私利,而且方式极端粗鲁,不顾后果。这种现象,上干扰中央的宏观调控,下侵犯百姓权益引发社会不安。
我以前一直在宏观经济部门工作,从国有资产管理局到体改办,见证了中国的财政改革、国有资产改革和金融改革。同样的特殊利益结合现象,给每项改革都造成了巨大损失。继财政、国资、金融之后,资源和环境是中华民族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我们在动荡的全球化世界上最后的战略储备。如果“老本”被劫掠一空,何谈民族的复兴?所以,“区域限批”针对的就是不顾国家大局的特殊利益结合现象。
记者:中央进行宏观调控,有些地方执行不力,是不是也与特殊利益结合现象有关?环保执法的重点行业钢铁、冶金、电力等与宏观调控的重点相吻合,特别是2007年,环保总局拿出激烈手段。这样做,除了保护环境本身,你们是不是另有醉翁之意?
潘岳:这是与宏观调控有关的。环保和“科学发展观”有天然的血缘,自然也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2005年环评执法之后,环评从“橡皮图章”变成了项目审批的重要环节,实际上已经成了宏观调控的手段。2006年仅环评一道关口,就卡住了7700亿元投资项目,其中一半以上是高污染高耗能产业。中央文件多次强调,要提高环境准入门槛来限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不正常投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这次使用“区域限批”政策,就是希望探索宏观调控的新方法。
屡败屡战
记者:但为什么“风暴”越刮越大,环境却越来越差。你和环保部门不停地刮“风暴”,是在乘胜追击,还是屡战屡败?
潘岳:肯定不是“乘胜追击”,也不是屡战屡败,而是屡败屡战。
2006年,环保总局是拼了老命的,我们强迫电力公司新建的脱硫能力是前10年的总和。我们什么手段都试过,从私下劝说,到通报,到叫停,到签署责任书,但仍然没有明显起色,为什么?经济增长方式没有转变,这不是一个部门“修修补补”可以解决的。
记者:每年的“环保风暴”,你们手中的大棒都不一样。如果明年还刮“风暴”的话,你们还有什么压箱底的灵丹妙药?
潘岳:没了。“区域限批”是最狠的行政手段,再往上,就该追究行政责任了,我们没有这个权力。
记者:很多人看来,你和环保总局招数不少,令人眼花缭乱,但似乎是花拳绣腿,不能一刀致命。“风暴”是非正常手段,难道就不能从制度上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吗?
潘岳:我最重视制度建设。目前的环保法律虽然多,但大都停留在理想主义阶段,惩罚权十分有限。行政手段上,环保总局不能关停,不能撤职,连环境监测和执法都没有垂直管理。要完善制度,开开会是不顶用的,只有博弈——每次环评执法都是博弈,对方退一点儿,我们就进一点儿,再用法律把成果固定下来。
比如说,第一次环评执法后,凡是发改委核准备案的特大企业的重点项目没有不履行环评程序的。此前,它们根本就不知道还有环评一说;“圆明园听证会”以后,《环评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出台了,2006年这个办法卡住了1600亿元公众不同意的项目;第二次环评执法后,环评由“项目”层面深入到规划层面,规划环评的法律在国务院法制办的审核之中,争取2007年上半年出台。这次执法后,我们希望能够把“区域限批”常规化——不只是每年一次,而是全年任何时候,对违规严重的企业和违规省份、地区严厉实行。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建立一个有效的新制度。
记者:这次“风暴”后,听说你的电话要被打爆了。“风暴”实际上是掐别人的脖子,断了许多人的财路和官路,你受到了什么样的压力?
潘岳:从两年前第一次环评执法开始,我和同事们就处在漩涡的中心。每年从我们手上要经过2万多亿元的项目,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内外压力都有。我就不多说了。
记者:妥协是为官之道,你会适当做出一些妥协吗?
潘岳:那要看妥协的价值。如果妥协能够造成新的制度,那就妥协。但如果是放弃原则和同流合污,那我决不!
记者:这几年,有些人观察你之后,得出结论:你并非像媒体上表现的那样强悍,实际上,你在硬撑着做事。比如说,在过去的“风暴”中,大唐国际就在名单中,这次“风暴”之前,大唐国际仍在违规,可见人们并不怕你。是这样吗?
潘岳:如果我是别人,我也不怕。环保总局既不能直接叫停项目,罚款也不能超过 20万元,不能撤官员的职,连自己的地方部门都管不了,怕它什么?就让它在媒体上喊两声吧,反正喊也是白喊,我们该干嘛还是干嘛。这就是现实。3年来,每当我看见违规的项目在补办手续后,用各种方法拖延兑现环保承诺;看见新的污染项目违法开工后,又打着“不能让国家受损失”的名义补办手续,心里十分沉重。但我不允许自己有“无力感”。既然法律和体制只给了我们这么大的空间,那我们就要在这个空间内创造出新的办法。现状决不能成为“无所作为”的借口,而是开展工作的前提。
顺便说一句,大唐国际电力已表示要彻底整改了。
官员和思想者并不矛盾
记者:有人说你是挑战风车的唐吉诃德。
潘岳:在实现理想的方式上,我不认同唐吉诃德,但在追求理想的精神上,我是钦佩他的。人最可怕的是没有理想,只被利益驱动。
记者:你当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时,清查海外国有资产和国有资产流失大案;当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时,开展“质量万里行”打击造假企业;当体改委副主任时,提出政改报告,呼吁宗教改革;任环保总局副局长没多久,就提出绿色GDP,刮“环保风暴”。这么多年来,你的执政理念是什么?
潘岳:我做的事情指向同一个方向——让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党,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民族,能够“可持续”。因为,一种生产方式、一个文化、一个党、一种主义、一个民族是否先进,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持续地强大。
记者:你似乎不仅想做官,还把自己定位为思想者——你写过政改报告,呼吁宗教改革,并研究生态社会主义。在思想方面,你想做出什么贡献?
潘岳:官员和思想者并不矛盾。在中国,只懂行政实践没有思想是不成的,只懂思想没有行政实践也是不成的。从少年时起,我就一直尊崇思想家。多年来经历了几次究竟是当学者还是当官的激烈思想挣扎。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说,支配人们行动的不是思想,而是利益。但正如韦伯说过:“思想所创造的观念,经常像扳道工一样,决定着利益火车头的行动轨迹。”历史上的大转折都是由思想作为先导的。中国正在经历伟大的转型,20年后的中国,是要成为拉美式的世界工厂和消费场,还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核心力量和价值观策源地?是将成为其他文明的翻版,还是创造出融合普世价值和自身传统的新型文明?这都取决于今天我们思想的方向。如果能够为它的诞生贡献一点微薄的火花,我此生无憾。
记者:但很多人批评你过于理想主义,你的很多想法是“乌托邦”——比如 “绿色中国”、“生态文明”。
潘岳:任何伟大的信念和事业,都是从乌托邦开始的。它就是对完美社会的追求。“乌托邦”做法不可取,但精神是必需的。在利益驱动的现实世界中,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推动变革的力量。
在朝在野,“家、国、天下”
记者:如果没有从政,你会做什么?
潘岳:最可能的是办报纸,或者做历史学家——既能描述广阔的历史,又能讲述动人的故事。我甚至可能写几个关于中国历史的大剧本。看到如今的那些历史大片,觉得我们的艺术家在历史素养上还欠火候。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改变世界的事件那么多,就是没人写没人拍。这是史家和文人的悲哀。
记者:你为什么喜欢历史?
潘岳:每一部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中国尤其如此。因为中华民族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以国家形态同根同种同文留存下来的民族,历史给我们的智慧和对我们的束缚都是其他民族所不能比的。前人遵循的规则,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依然发挥作用;前人遭遇的困境,今天依然没能全部解答。历史的每一次变迁,都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执政者应该善加吸纳。
记者:你的风格也与其他官员不同,你经常说一些似乎“出格”的话,爱好不少,写散文,还写古体诗。我在你的诗文集中看到了这样的句子:“古寺灯影,三佛并坐,东琉璃西净土,沉浮众生轮回相;楼观经藏,大道同源,左庄老右程朱,彻悟天地解自身”;还有这样的句子:“漫天情絮,乱乱夜无语。颜色一分天给予,不怕梅花香许”。你像个文人,而不是官场中人。
潘岳:官场中的人就是木头吗?很多领导同志都喜欢诗词,有些写得还很好。我们一直习惯了模式化的官员形象,其实私下里大家性格都很丰富,只不过我的生活更加透明,你们对我的了解多一些罢了。我从少年时代一直坚信,不管你是官员、学者还是别的什么,首先你是一个人,一个性格完整、有信念、有感情的人。
记者:你喜欢历史,也熟悉媒体,这两个领域都密切关注社会的变迁和变迁背后的推动力。据你观察,现在改变中国社会的最大新生力量是什么?
潘岳:互联网。网络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进而改变了社会和政治运行的规则。最重要的是,网络孕育出的新一代人,尽管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他们总的来说,视野更加宽广,思考更加独立。
记者:你觉得那一代的执政者要具备什么素质?
潘岳:他们要善于学习新事物、接受新理念,并倾听人民的声音。更重要的是,在一个越来越“个人主义”的时代,必须具备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在多数人可以在个人生活中获得满足的时候,他们必须视民族的兴衰甚于个人荣辱。
记者:兼济天下,而不是独善其身?
潘岳:对。这是中国政治传统中最优秀的部分。对一个大国来说,无论哪一个历史阶段,都要求执政精英具有特殊的责任感,儒家在这方面值得借鉴。我也有“士大夫”情结:在朝在野,都是“家、国、天下”四个字。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教师登录
教师登录